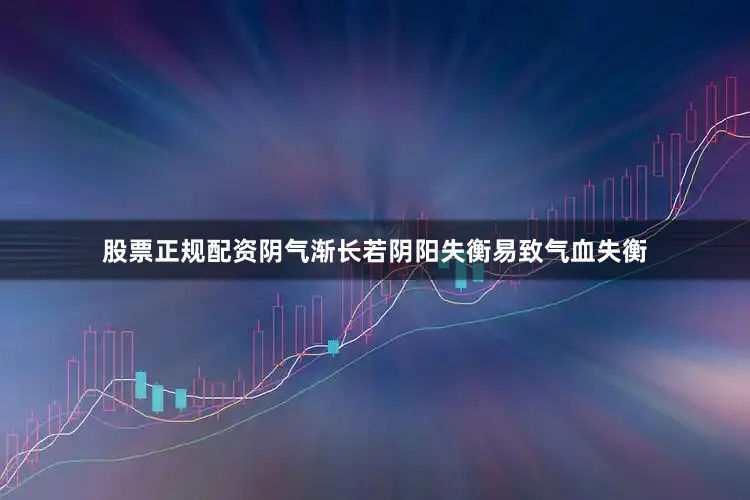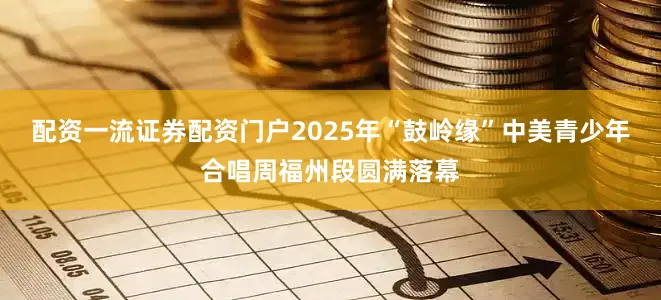“1958年2月3日,下午三点,你今年多大?”毛主席靠在沙发扶手上,笑眯眯地问眼前这位身着军装的余秋里。听见“43岁”三个字,他摆手:“儿童团嘛,嫩点不要紧,锻炼!”一句玩笑,把紧张气氛冲得无影无踪。

那是建国第九个年头。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收尾,钢铁超额完成,化肥也跑赢指标,唯独石油挂了红灯——年产不过300万吨,缺口巨大,锅炉烧柴火已成常态。毛主席心里急:“油不够,工业就喘不上气。”他和周总理、彭德怀商量,要从军队抽一名年轻将领来“破局”。条件只有三个:能吃苦、能聚人、敢拍板。
彭德怀点名余秋里。这个江西小个子打过长征、整过后勤,抗美援朝时管过弹药米袋,也管过医院手术刀。周总理同意后,按惯例先打招呼。“中央看上你了,准备接李聚奎的班。”余秋里愣住,憋出一句:“我没摸过钻机,怕误事。”话虽谦逊,却难掩血性。 几天后,颐年堂那场对话敲定了人事命令。毛主席补了一刀玩笑:“部长以上干部调动,不叫转业;真要转业,还得给你发笔钱呢!”一句轻松收尾,余秋里只能笑着敬礼:“服从组织。”

3月1日,新部长拎着一个帆布挎包走进石油工业部。他没要独立办公室,让人把椅子搬到李聚奎对面,同用一张旧桌子。开会,他不插嘴,只做笔记;晚上,把白天听不懂的地质术语抄在小本子里,拉着专家到家里“加班开小灶”。十来天,楼道里便传出两种声音:一种夸他肯学,另一种嘀咕——“老革命能打仗,干工业恐怕外行。”
第一次干部大会正好撞上这种杂音。会场人声嘈杂,女同志打毛线,小伙子低头写信。余秋里按捺住火气,温言讲话收场,掌声稀稀拉拉。半个月后,他再度点名开会。前半场仍是云淡风轻,突然一拍桌子,麦克风砰然作响:“有人说我不懂石油,李聚奎也不懂。可我问一句——你懂没有?骄傲不是本事!”短短几句,场内静得只剩呼吸声。接着他抛出两条原则:天然油为主、人造油为辅;勘探布局先选择一个突破口,必须打开新局面。会后机关传话:“新部长发了火,像个炮筒子。”

炮筒子很快对准了作风散漫。教育司写给外交部的公函,把“外交”误写成“郊交”。余秋里拎着信封在会上甩了半圈:“这是谁批的?”副司长顾德勤起身,脸涨得通红。余秋里严词批评:“凡机关干部出问题,先问领导。”震慑之余,也立规矩。
制度立住,方向更要准。西南找油的好消息没撑几个月便落空,油井喷几天就哑火。1959年底,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,余秋里汇报时低声说:“产量不理想。”毛主席却拍拍椅背:“东方不亮西方亮,中国这么大,总有油。”离沪返京,他立刻求教李四光。地震勘测图摊开,李四光指向松辽平原几个圈圈:“杏树岗、萨尔图、喇嘛甸子,下边可能有大油。”余秋里听完,连叼香烟的动作都轻快起来,当即决定把赌注压到东北。

1960年初,松辽石油勘探局挂牌。副部长康世恩坐镇前线,提出“提前完井试油”,苏联专家坚决反对。电话线那头,康世恩只问:“拍板吗?”余秋里盯着办公室墙上那张全国油气分布图,沉默一夜,次日清晨回电:“按你方案。”9月26日,萨尔图原油喷出棕褐色“火龙”,大庆油田露出真容。事后专家复盘:若按苏联流程,油层可能被泥浆压死,发现至少推迟两年。
油找到了,人手却不够。全国石油工人不到四万人,大庆开发至少要翻倍。余秋里想起旧战友,飞去广州请示中央,很快批复三万名退伍官兵归属石油部。3月初,大会战队伍浩浩荡荡抵达萨尔图。寒风零下三十度,树梢结冰。食堂里高粱米冻成疙瘩,干部战士依然挥铁锹、抬管线。“实践论”“矛盾论”学习班每天一小时,余秋里自己站讲台,有时嗓子哑得发不出声,工人递茶,他摆手:“继续。”

条件艰苦得难以想象。指挥部搭在旧奶牛棚,夜里雨水顺着瓦缝滴到床铺,余秋里被浇醒,拍拍水盆打趣:“这点小雨,跟长征比算什么!”有人饿得直不起腰,他拎着勺子跑厨房:“伙食先抓好。”遇到技术难题,他干脆蹲井口陪班。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那幕,正是他在场。“向铁人学习,人人争做铁人!”口号经话筒传遍荒原,极大提振士气。
1000多个日夜,700多口采油井拔地而起,1964年原油产量达800万吨,新中国“贫油国”帽子被扔进历史垃圾堆。国务院工作报告里,周总理声音铿锵:“中国人民用‘洋油’的时代结束了!”这一刻,余秋里坐在人民大会堂后排,轻轻抿了口白开水,脸上没太多表情,只把笔记本合上——上面写着三个字:任务完。

回头看,毛主席那句“嫩点不要紧”并非一句随口调侃,而是对干部年轻化、专业化的信心。事实证明,余秋里“外行”办石油,并非依赖个人天赋,而是靠吃苦、用人、敢担责。43岁接过烫手山芋,五年后交出大庆答卷,这样的“嫩”,正是国家急需的新鲜血液。
驰盈配资-正规股票平台-配资股票推荐-配资天眼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全国十大配资平台由迪丽热巴领舞的《天女散花》
- 下一篇:没有了